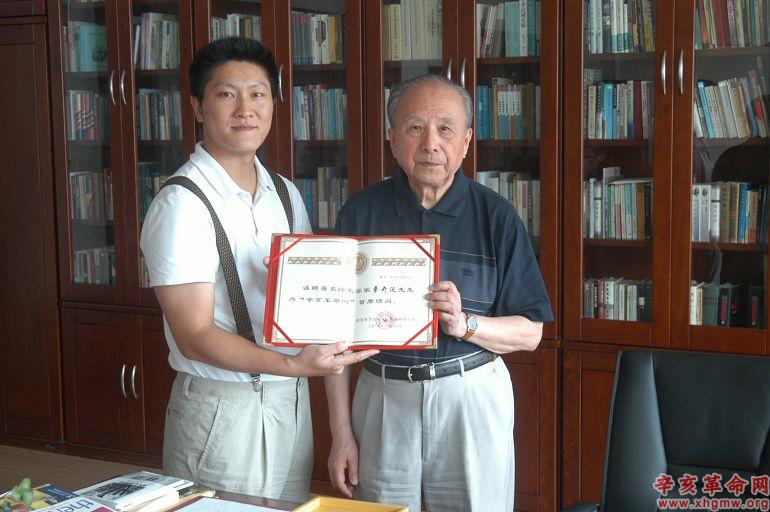《辛亥首义史》(连载2)(4)
三、短时段“首义”造因于中长时段社会变革
武昌新军暴动事起仓促,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,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、文学社的首脑也或伤(如孙武)、或亡(如刘复基)、或在逃(如蒋翊武),事变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,带有很大的“猝发”性质。
然而,偶然寓于必然之中——
武昌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,举义者能够迅猛而有序地展开战斗,有条不紊地占领省会城市,及时建立新政权;
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,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;
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;
湖北军民在湖南等省支援下,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装备精良的久练之师——北洋清军周旋于江汉之滨、龟山之麓达四十多天,从而为各省“易帜独立”赢得宝贵时间……
这一切则无法用“偶然性”一言以蔽之。当我们考察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(尤其是中心城市武汉)出现的新的经济结构、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,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的期间,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,在乡邦所作的英勇而坚实的努力,进而注意地望形胜,便会发现:辛亥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。
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(1902—198)提出历史研究“时段”理论,即区分地理时间(长时段)、社会时间(中时段)、个体时间(短时段),又将三者分别称为“结构”(structures)、“局势”(conjunctures)和“事件”(evenements)。主张重视地理时间(“结构”)、社会时间(“局势”)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,个体时间(“事件”)为结构与局势所左右。而传统史学较多注目于“个体时间”,主要用力于重大政治事件、外交活动、军事征战等“短时段”事变的研究,这显然是有缺欠的。今日我们作辛亥首义史考辨,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,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,从结构、局势、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。
费正清编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:
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—1913年阶段,不应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—1912年阶段。其次,根据这种广义的概念,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象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。[14]
主张将辛亥革命史追溯到1900年以来(约为清末新政时期)发生的社会变化,此说有理,但还应当扩大视野。
考察辛亥革命,当然需要细致入微地梳理1911—1912年间发生的“短时段”剧变,但还须追究其背后的 “中时段”社会结构造成的久远影响,考察19世纪60年代汉口“开埠”以来,尤其是考察1889年张之洞(1837—1909)总督两湖、主持“湖北新政”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,考察兴实业、办文教、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造成的经济、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;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,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,辨析辛亥首义史的启承转合。
本书在全面观照“结构”(structures)、“局势”(conjunctures)制约 “事件”(evenements)的前提下,特别注意社会时间(中时段)对个体时间(短时段)的影响力,注意这种影响的复杂性。例如,张之洞殚精竭力主持“新政”,是社会时间(中时段)发生的大事变,张氏操办湖北新政,主观动机当然是维护清王朝及纲常名教(其所著《劝学篇》内篇有明白宣示),然而,这些近代性事业导致的客观后果却出其意表之外。
仅以练新军而言,张之洞为的是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,他于19世纪末叶派遣姚锡光(1857—?)、吴殿英(1842—1907)、张彪、黎元洪等赴日本学习近代教育(重点在军事教育),随后又派吴禄贞(1880—1911)、蓝天蔚(1878—1922)等武备学堂学生入日本军事学校留学,由此获得编练湖北新军的模式,试图以一支装备、训练西洋化的军队挽朝廷衰败于既倒。然而,这样一支初具近代文明属性的湖北新军,却不以张氏意志为转移,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温床,至辛亥革命前夕,湖北新军士兵约三分之一参加革命团体,三分之一受其影响,仍然被清方掌控的不足三分之一。辛亥首义是一次从新学堂走出来的知识分子“投笔从戎”,在近代城市军营发动的新军起义。而“近代城市”、“新学堂”与“新军”正是张之洞主持的“湖北新政”的产物。孙中山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,于1912年4月来武汉访察,睹物晤人,发现正是直隶南皮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,为辛亥首义奠定了物质基础、准备了人材条件,故孙氏由衷感慨: